写在前面:本文原载于萌娘百科新媒体专栏(2022年5月2日),专栏登载版本相较本版有小幅改动。专栏版链接:固守、固守、还是固守:简评《泡泡》
以下正文。
2019年,中国的动画学者赵冰出版了一本影评类书籍,题为《固守与超越:美日动画电影母题研究》。翻开这本书的目录,读一读其中提到的日本动画电影母题:“国民少年”、“无垢的少女”、“边缘人”、“义理与承受义理”、“异类幻化”、“生活的小确幸”、“灭亡与再生”、“异世界的存在”、“未来世界”、“人与自然”……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是的,将这些业已固化为极其传统的普适情节的母题连缀在一起,我们便得到了这部极其传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老套”的动画——《泡泡》。
约莫半年前,当我看到这部作品初创的消息时,点进STAFF列表,众星云集所带来的强烈压迫感向我传来:这仿佛继承了国家队的光荣的传统,《DARLING in the FRANXX》《甲铁城的卡巴内瑞》等等作品在这一刻灵魂附体,在这一刻这部作品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于是乎,感动万分的我在萌娘百科该作品的评论区留下了一条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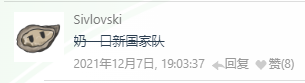
这条评论现在是热评第一了。
当然了,我们大可以纵情地赞赏这部作品中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可否认,在跑酷的作画方面和整体的配乐方面,《泡泡》的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整体的价值观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正。让我们来扩充一下前面所提到的叙事母题:“国民少年”——男主角,“无垢少女”——女主角,“异类幻化”——女主角从泡泡变成人,“灭亡与再生”——故事的结局,“人与自然”——剧情整体走向所传达的价值观……有了这些传统且正面的母题支撑,《泡泡》自然拥有着叙事情节的稳定性。
这种叙事情节的稳定性虽然可以保证整部作品的内容不至于滑向极端烂作的悬崖,但也使得作品在剧情上变得极为平庸——这种平庸不是《小美人鱼》的故事来源所造成的千篇一律,而是追求商业性所带来的叙事角度的无可挽救的平庸。当一部在2022年诞生的众星荟萃的作品中的所有元素都是对几年前学术书籍中动画刻板印象的拙劣翻版,这难道不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悲哀么?有很多人说这部作品是所谓的“致敬新海诚”,但实际上这种对商业动画电影的形象固化并非仅是新海诚的爆火所产生的,而是长期以来日本动画在叙事上的传统所积淀下来的创作范式;不幸的是《泡泡》几乎在每一处地方都迎合了这种创作范式,这便成为了其高扬的商业性与低劣的叙事性的原爆点。它不仅仅是“致敬新海诚”或是“致敬宫崎骏”,它成为了整个日本动画电影叙事中所谓“精华”的凝结产物,而这恰恰就是它平庸的原罪。
当我们看到这样豪华的STAFF阵容时,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看到荒木哲郎,我们想到的是《死亡笔记》《进击的巨人》;看到虚渊玄,我们想到的是《沙耶之歌》《魔法少女小圆》;看到泽野弘之,我们想到的是《aLIEz》《βίος》……我们想要得到的不是名角联袂呈上的五彩斑斓的黑,而是不同的动画创作者们所展现出来的对于动画艺术和叙事本身的理解与奉献。遗憾的是,《泡泡》所带来的只是一些迎合商业化的模块化母题拼接,“固收与超越”中的超越似乎还是泡泡,未能幻化为无垢的少女。
我们尚且会为这种固守所带来的平庸而呐喊,而商业化与所谓“文艺风”却已经快要把这种“爆米花电影”推动成为主流,成为让更多初次接触日本动画电影的人所迷恋的第一印象。一些叙事桥段成为母题不是为了让后来的创作者们去反复的使用它、拼接它,而是不断地去深入挖掘某个母题之下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呼声。我们为何会对《泡泡》失望?本质上也是对于所谓“商业动画”在叙事、作画等等方面上陈腔滥调的失望与对打破固有母题作品的期待。
最后,引用加拿大动画家弗雷德里克·贝克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不少动画片……从动作、特技效果,直到一连串的活动,什么意思也没有表达出来。世界需要释疑解惑,但是动画片却在利用各种技术生产……动作和空虚。”《泡泡》之上,是商业的浮华众生,更是固守传统叙事的悲哀。
我们理应呼唤更多比《泡泡》更加在云端行走的动画作品。
参考文献:
- 赵冰. 固守与超越:美日动画电影母题研究[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9.
- 寇强. 动画民族意识与地域文化[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
